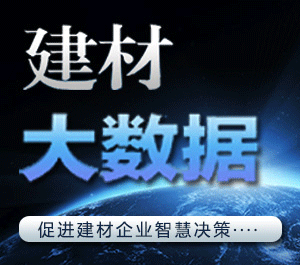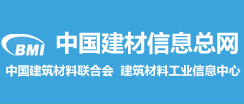藏在砖瓦堆里的这只熊 有故事 |
|||
| 来源:《广州日报》官方帐号 发布时间:2022年01月18日 | |||
| 摘要:
那些砖头瓦块,里面有很多宝贝 |
|||
|
南越国宫署遗址中,不太为人所注意,但意义非凡的,是那些砖头瓦块,里面有很多宝贝。 比如一件熊饰空心砖踏跺两端的熊饰。它也是新近出炉的中国考古百年广州百件精品文物之一。
从图案上可以直观地看出,熊纹主体表现了熊头部的图案,熊两眼正视前方,炯炯有神,前后掌紧握、并列相聚、威武有力,活灵活现地塑造出熊的形象,特别突出头和掌的作用。因为卡通影视的宣传,熊这种动物在部分小孩子看来相当“萌”,城市生活中的一些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种攻击力很强的猛兽。在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熊饰空心砖,也有这种两面性,一方面似乎有些憨态可掬,另一方面又比较霸悍威猛。
《周礼·天官·司裘》记载:“王大射,则共虎侯、熊侯、豹侯,射其鹄。诸侯则共熊侯、豹侯。卿大夫则共麋侯。皆射其鹄。”王之射礼以“三侯”即虎、熊、豹,诸侯射以“二侯”即熊、豹,卿大夫射以“一侯”即麋,士射以犴为侯。学者指出:所谓“侯”者,指不同的兽皮装饰制作的箭靶,实际是田猎时贵族等级的符号标志。熊在百兽之中的突出地位,令它在尊崇尚武精神的汉代成为一种特殊地位与身份的象征。 关于熊的装饰,在南越国时期的其他出土文物中也见到不少。南越王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馆员霍雨丰在《南越王墓的动物世界》中就进行了归纳:“南越王墓西耳室的熊图案出现在节约中,节约是车马器中马饰的饰件,南越王墓的熊形节约主要有两种图案,以及大小不同的式样。两组图案的熊形节约都呈半球形,球面所铸的熊突出熊首和四爪,呈蜷缩状,也像在啃咬的样子。”他指出:“这类熊形节约,和其他汉墓所出的熊形节约基本一致,如河北满城汉墓、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等。此外,南越王宫所出的熊饰砖,和南越王墓节约上的熊形一致。” 此外“西耳室的一件玉珌的一面有一熊浅浮雕熊纹,这只熊双掌拉着螭虎尾,并用口衔咬,作嬉戏搏斗状,表现极为生动。此外,东耳室和西耳室出土的3组共12件铜瑟枘,呈博山形,每一件都有若干动物造型环绕其上,其中就有熊蹲坐着。” 霍雨丰还指出,熊形和熊饰在汉代出土文物中常见,最常见于各类铜、陶用器的器足,此外,也见于镇、节约、砖等器物之上,“这些熊饰表现欢快,似乎反映了汉代生机勃勃的气息。” 有研究者指出,现存的汉代遗物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熊图像,形态各异、配置多样。体现出熊在汉代身份的多重性、地位的特殊性。在汉代之前的古史中,有大熊伏羲氏、黄帝有熊氏、鲧禹化熊等神话,都提示中国上古时代应当有一脉与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,且中华文明起源与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;红山文化等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玉熊、陶熊、熊头骨等,都是与这种文化有关的证据。 具体到汉代,汉代人将熊图像施于画像石、画像砖、壁画、玉器、摇钱树等各种艺术形式之上,配置在不同场景中,有刻画在西王母旁的熊图像;有出现在祥禽瑞兽间的熊图像;有手持鼓槌状物的熊图像;有蹲坐支撑器物的器足熊;有击掌舞蹈的熊图像等等,实际上也是一种远古熊文化的遗风留存。 文/广州日报·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/广州日报·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视频/广州日报·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广州日报·新花城编辑:李亚妮 |
|||
|
|
|||
| 版权与免责声明: 本网站注明“来源:中国建材信息总网”的文本、图片、LOGO、创意等版权归属中国建材信息总网,任何媒体、网站或个人在转载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,违反者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。 凡本网注明“来源:XXX(非中国建材信息总网)”的作品,均转载自其他媒体,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对其真实性负责。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,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,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无意在本网发布,请在两周内与本网联系,本网经核实后可立即将其撤除。 |
 微博
微博 微信
微信 移动
移动